■杨 信
明代书商余象斗在《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》扉页上印着"刻书传世,以文养文"八个字。这位科举落第的书生将四书五经与算盘账簿并置,在书卷与银钱间走出第三条路。六百年后,我们依然需要这种智慧:读书与赚钱本是一体两面,前者是思想的锚点,后者是生命的压舱石。
北宋文人苏舜钦用"汉书佐酒"的典故惊艳了历史。他将读书视作精神盛宴,却因不肯与权钱交易而遭贬谪。这个悖论般的困境至今未解:当知识分子将铜臭视为洪水猛兽,实则陷入另一种蒙昧。正如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揭示的,市场的无形之手不仅调节商品价格,更在塑造现代人格。读书人若不能参透货币流动的密码,其思想终将在象牙塔中干涸。
扬州盐商马曰琯的藏书楼藏着令人震撼的启示。这位乾隆年间的商界巨擘,既精于淮盐贸易又醉心典籍校勘。他的"丛书楼"藏有十万卷古籍,却从不将藏书与账簿分隔。这种知行合一的智慧,恰如普鲁塔克笔下的希腊商人:"他们在甲板上读荷马史诗,在账簿里写哲学笔记。"当知识成为商业航船的罗盘,利润便不再是肮脏的脚印,而是文明进步的刻度。
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痛陈"士不知兵,农不知书"的弊端。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,这种割裂更为致命。硅谷创业者的案头总摆着《孙子兵法》,华尔街交易员研读《道德经》寻找市场韵律。真正的高贵,在于让知识在市场中淬炼成真金,让财富在书卷里沉淀出光华。这不是堕落,而是将苏格拉底的追问带进证券交易所,把庄子的逍遥游写入商业计划书。
敦煌藏经洞的经卷与丝绸之路上叮咚作响的驼铃,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的进行曲。当我们翻开《国富论》,不该忘记亚当·斯密同时是道德哲学教授;诵读《论语》时,当知孔子门徒中不乏子贡这般商业奇才。读书与赚钱的修行,本质上是将星空装进行囊,在尘世走出最踏实的足迹。这种完整的人格修炼,或许才是对抗时代虚无主义的真正法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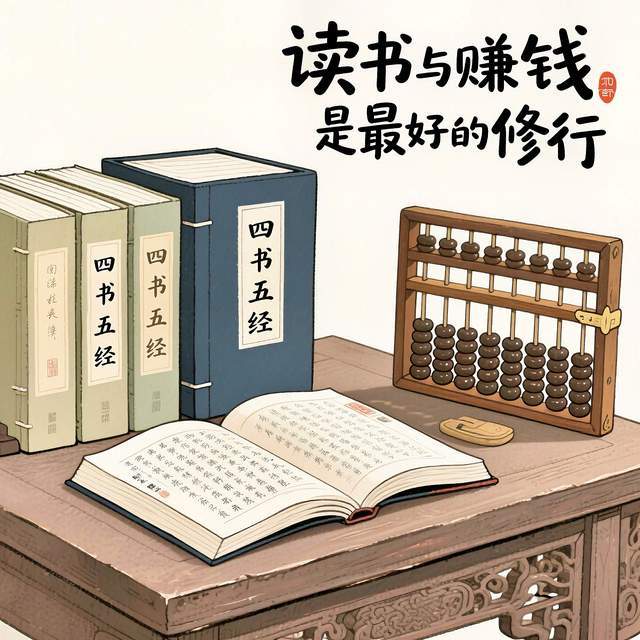
编辑:景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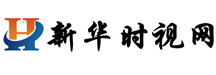 | 企业视窗
| 企业视窗 




